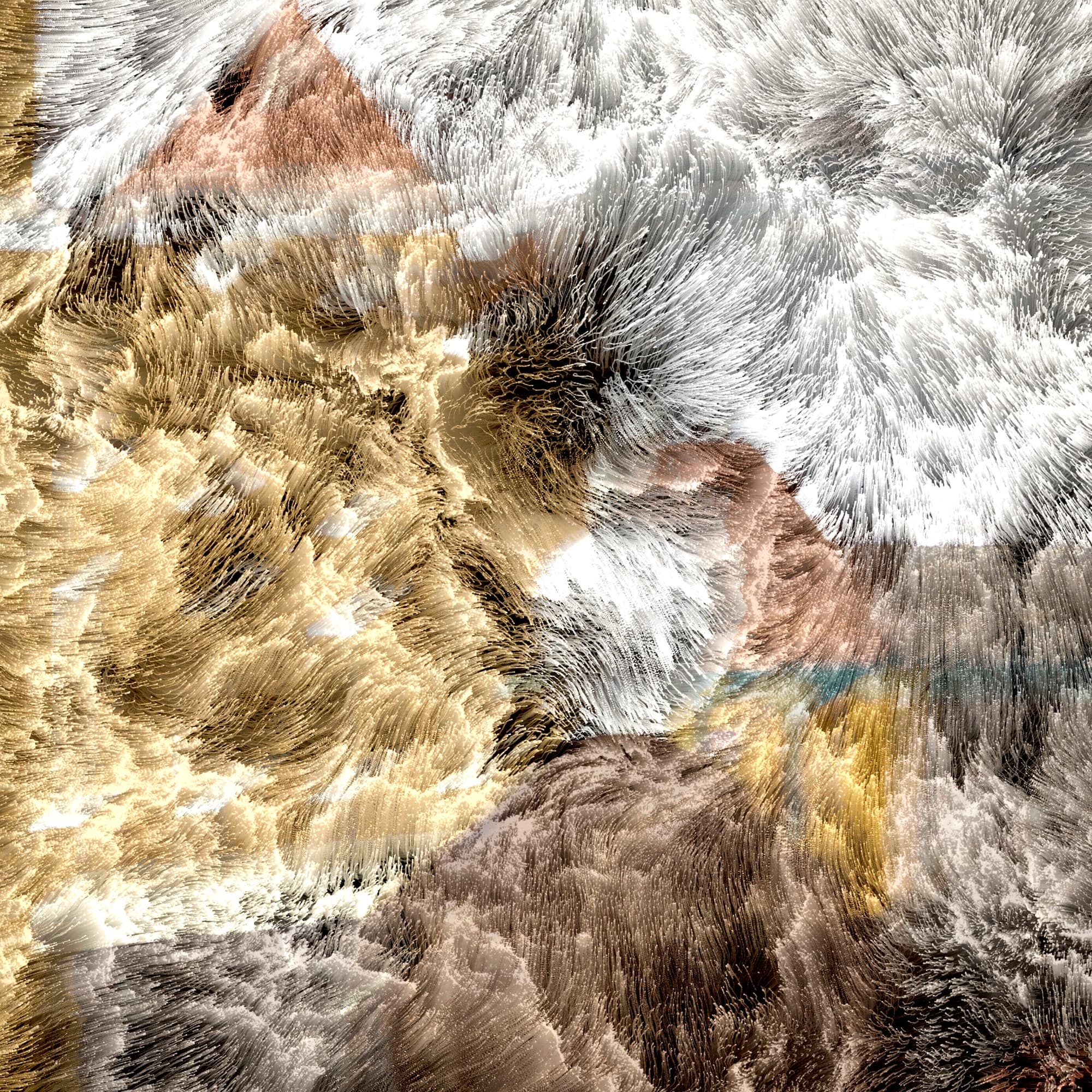伍韶劲以光影和声音装置,呈现平常或被忽略的事物。《蒲絮》是场域特定作品,回应这个地方的历史。在启德机场尚未落成之前,新蒲岗称为「旧蒲岗」,有传那里是一片蒲田,蒲絮在空中飞扬;之后,蒲田变成旧机场的跑道,航班在那里起飞降落。动态装置《蒲絮》于AIRSIDE中庭徐徐升起和飘落,宛如时间中的轮转。像麦树坚的散文〈早晨的气味〉,为生活中的熙来攘往,带来清新的气息。
蒲絮
.jpg)
| 流 | 轮 | 转 |
织织如流 纺一城轻暖 | 茫茫时百折千迴 飞絮流连轮转 | 光亮有时 高飞有时 |
动态时间 1pm, 6pm | 动态时间 2pm, 7pm | 动态时间 3pm, 8pm |
偶然起床起得早(其实未必有睡过),决不会磨蹭在家等到日光普照才外出活动,总是胡乱穿件外套、换过波鞋到楼下吃早餐、买报纸。有时候我会随便戴一顶鸭舌帽,遮盖蓬松凌乱的头发──不过,顺其自然、不修边幅的时间还是佔多数。我本来就不是一个讲究衣着的人(外套、上衣、裤子和鞋袜总是胡乱拼凑),又完全没有时装触觉(有时我还会穿十多年前买下的衣服),所以我清早的造型可说是十分糟糕的。
七点以前,街上的早晨气味浓得嚣张跋扈。植物的绿意随第一口吸入的空气大举攻陷鼻腔,将「运作」的讯息灌进人的身体里。我总觉得这种清新气息是粉末状的,很疏离地分佈在空气中,由于很轻,就被人们一点一点地吸进肺里,又或者黏附在衣物上,直至到达热闹的地方如车站或巿场才融化。这种气味通常是又湿又凉的,那不过分的寒意略带灰色,好衬托其他颜色逐步转醒。树木从黎明的昏暗中重新拿出树榦的白与啡,拿出叶片的碧绿或墨绿,它们才显出细緻和层次;道路从街灯的监视下逐步获释,还原它们的深渊黑和斑驳灰,掌握它们的弧度和斜度。一丛又一丛季节的花,通往公园的捷径,舞着羽毛扇的仁慈长者,穿梭于高处低处的雀鸟……冉冉从灰色里浮现积存了一夜的活力。
八点以后,早晨的气味急剧消散,直至没有味道就是白昼的味道了。夏季昼长夜短,早晨的气味来得早,消散得更早。五点钟起床往外边一张,天色已经转淡,不消片刻,整片天就全亮起来。
小时候总有到外公家小住的机会,外公外婆例必会带我去吃早茶。外公爱帮衬蓝地街巿附近的嘉爵酒家,那里有称呼他做「阿黄」的老朋友。沿青山公路经过桃园围的田边,空气特别清爽,能与繁忙车道的汙浊废气抗衡。也许是那儿植物特多:最外围是猖獗的野草和不知名的树木,里面一层是假芋头和蕉树,中间是农人栽种的蔬菜。那条路的空气之所以特别,全因植物气息里渗有纤纤流水的味道。你很难看清楚水的起迄处,在土地里如何曲折发展,但总能嗅到它的存在,抓到一种属于新界的水独有的味道。
早晨的气味最有效使我忆起读中学的时光。那时候我有六点前起床的习惯,梳洗、更衣的动作再温吞吞也能六点多到达车站,车开得再慢也能七点前抵达目的地车站。连接学校和车站的路呈L字型,每朝准时有个古怪大叔把鞋子挂在颈上,以倒后走的方式走几次来回。一同回校的几个同学,都说明天在路上放几颗图钉吧,可是说了几个学期都没有实行这恶作剧。我对这段路印象深刻不全因为这个怪人,而是那股早晨气味令我精神抖擞。那条路犹如一张展开的白纸,叫我放心写下当天所得的知识。学校临海,风势不分季节的清劲,偶尔单衣上学,寒意似是劝学的训示。那条路上有列车的铃声、麻雀的啁啭,都很清脆;前半段路有青草味,中段就飘来中式早点蒸腾的气味──糯米鸡比较高调,肠粉淡雅朴素,烧卖和粉果相对地鬼鬼祟祟,所以输给山竹牛肉。
冬天校工开门的时间比夏天要迟。我们经验丰富,慢慢买好了早餐,踱到校工宿舍附近就同声大叫:「阿婶开门呀!」可怜的阿婶犹在温暖的被窝里造着好梦,却被我们几个顽皮鬼吵醒。睡眼惺忪的阿婶匆忙围上颈巾、穿上晨褛半跑半跳冲出来开门,每次都喋喋不休骂我们残忍呀苛刻呀不近人情呀。我们捧着塑料保温碗喝着冒烟的皮蛋瘦肉粥,笑说:「阿婶,我们刚才见到校长,你不是要他叫你开门吧?」阿婶那副悻悻然咬牙切齿的表情,令我们几个乐不可支。
成为全校最早上学的学生其实没甚麽了不起。霸佔了有盖操场的桌椅,不是吃早餐就是做功课(本来昨晚就要完成的功课),遇上测验就姑且在这一小时努力一下。间中有同学带篮球回来,我索性把书包丢在篮球架下,在清凉的空气中比试飞身上篮和急停跳投。难得空落落的校园,篮球弹地的迴声,脚板透过鞋底感受到的摩擦与震盪,三者糅合为一,至今仍然被我奉为青春期的重要标誌。
唸中学的七年里,我每天游刃有馀、轻轻松松的上学,一次迟到的纪录都没有。永远与训导主任缘悭一面,或多或少要归功于老爸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」的训勉。在家里,老爸就是无上权威,对于他的训诫我不敢忤逆。但是老早回到学校吃过早餐就无所事事,除了聊天,便只有在球场上拼个你死我活。尚未上课,衬衫就湿得贴着背嵴,早起的得益不过是发现几个有把握的射球位置。
为了早起,更加要坚持早睡,结果惹来同学嘲笑。有同学晚上九点钟打来我家问功课,我却好梦正酣。接电话的老爸答道:「麦树坚已经睡了。」翌日回到学校,我旋即被同学围着嘲笑是听教听话的笨小学生,后来还被质疑是不是有甚麽难以启齿的暗病。
后来我反複思量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」:第一个想法是早睡早起的最大好处是身体健康,而所谓抢佔先机不一定斗快斗早,还要论实力、比智慧,甚至看谁运气好。第二,若对照「愚鸟先出林」,那麽要早起才有虫吃的鸟不只是蠢,应该也很羸弱。要承认自己智力低下、身体孱弱是需要勇气的。第三,谁说早起就等如担当「鸟」的角色?说不定本来就是条「虫」──「早起的虫」,不过是成全「早起的鸟」的牺牲品。因此懒虫迟迟不起床,其实未必没有审时度势的睿智。
唸预科时我依旧是愚鸟,因为转了学校,上学的路便突然寂寞起来。没有再在球场上飞来飞去,每天乖乖吃过鸡蛋三明治便开始温习,应付生生不息的小测。
唸大学时,我起床起得更早。未够五点我就起床,蹑手蹑脚梳洗后亮着书桌的灯,读那些与学业有关或无关的书。此刻家里真能一点声音都没有,我能集中精神阅读。然后清晨的气味由窗户渗进屋里,传来一点凉意,书纸因此洁白起来,让人不忍掩卷。这时期老爸不再谈甚麽早起的鸟,改以有典故的「闻鸡起舞」勉励我继续早睡早起。有祖逖和刘琨的故事支持,我没有再想到早起的虫了。
有时候我也会在清早回复隔晚的电子邮件。老师收到我的回复十分惊讶,她在自己的专栏里叹息:「清早上网,往电子邮箱一看,赫然是你的来信。发信时间是早上五点多……今天还有坚持每天天亮前起来读书的孩子?」我的答案是:「我从不晚睡,我只是早起」。这是我的生理习惯,已经成为我生活的规律了。当然,我承认我惧怕玩乐,心底常存歉疚,总觉得自己的光阴流失得比别人快,所以同龄朋友喜欢的玩意和娱乐活动,我几乎没有参加。进大学的第一天我已有明确目标,我知道这个目标很稳妥、安全,虽未至于万无一失,但必定没有错。
早起的习惯一直坚持至任职自由工作者(freelancer)才终结。为了赶在限期前完成任务,我经常日夜颠倒、夜以继日,通宵达旦不眠不休去消化工作。未必有连续六小时的畅快睡眠,能小睡片刻已经很不错了。我有好几次这样的经验:在清晨六点完成了艰钜任务,把成果发送给「买方」后有大罪得除的释怀。因为错过了入睡的最佳时间,因为肚饿,因为想喘口气,便随便换过衣服走到街上,呼吸能令我忆起美好青春期的早晨气味。
早晨的气味,这些年来不曾变易,无论我搬到哪儿,只要我没有患伤风,那股气味万试万灵能令我重新振作。身体再疲累,精神再萎靡,深呼吸几下把肺里的鬱闷换掉,眼睛就能明亮地睁开。
从容地吃饱早餐,回家一开门就看见老妈在柔和的日光中踱步。她还未架上眼镜,眯着近视眼扫视我手里的报纸和麵包,过了几秒又老调重提:「怎麽又不梳头就跑出去?」
「这是近期流行的发型嘛。」我已经习惯这样回答。
伍韶劲(1980年出生)为跨领域艺术家及设计师,擅于创作概念性、场地特定和参与式项目。他相信艺术不但与社会有着密切关係,更可以改变社会。这种信念一直驱动着他的艺术创作。他的作品曾于广州三年展、上海世界博览会、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、米兰设计週,还有法国、意大利和澳洲等多个大型国际展览中展出。在加拿大怀雅逊大学取得新媒体艺术系学士后,他先后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及法国国立当代艺术工作室Le Fresnoy 取得可持续设计理学硕士及艺术硕士文凭,并自2015年起,加入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院担任助理教授。
麦树坚,香港浸会大学荣誉文学士、哲学硕士。曾获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、大学文学奖、香港艺术发展奖艺术新进奖(文学创作)、中文文学创作奖及中文文学双年奖等。着有散文集《对话无多》、《目白》、《绚光细泷》、《板栗集》;诗集《石沉旧海》;小说集《未了》、《乌亮如夜》等。
.jpg)
作曲:林丰
灯光设计:李智伟
技术总监及製作伙伴:金舞台技术有限公司
单簧管:冯逸山 / 小提琴:陈诗韵
大提琴:李帼珊 / 钢琴:严翠珠
特别鸣谢:黄子珏、林池、张嫣玹、王嘉敏、张慧婷、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院